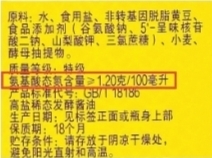我真的畢業了嗎?
時間:2024-10-19 來源: 作者: 我要糾錯
父親是北方一所高校的老師,還當了幾年班主任,那幾年,家里總有學生來找,談理想談人生談學期成績,最后在晚餐前懂事地告辭離去。我單單記得一個戴眼鏡的女生,一個白白凈凈的上海人。因為她肯走到我身后,看我寫作業,小學生的作業,還問起墻上花花綠綠的畫片是誰貼的。我承認是我,于是得到了她的夸獎,說是比女孩子弄得還細致。我從小就是有虛榮心沒自尊心
的孩子,人家拿我與女孩子比,我不覺得恥辱只覺得幸福。后來這位姐姐不來了,我問父親,說是已經畢業了。那時候才留心這個詞,才明白畢業就意味著離散。
那位姐姐自然就沒了消息,我人生中再有什么斬獲,都不可能得到來自她的表揚。后來讀鐘曉陽的小說《流年》,其中這樣寫葉晨和江潮信一生的緣分:“她小他五歲,他少年她童年,他青年她少年,長長到底趕不上。”二十四個字,概括得真精當。
當然我也就一次又一次的畢業,一次又一次品到了離散。就算海內陸續存過知己,可我也終于明白,天涯不會若比鄰,天涯就是天涯,有時候轉身之處就是天涯。
小學畢業還沒有什么知覺,只擔心自己上不了重點初中。也就真的沒上成,于是初中過得比較爛漫無負擔。到初中畢業,班里人手一本畢業紀念冊,許多同學才發現,自己平時儲存的名言警句還是不夠用,紛紛向我乞討——于是,恍惚間我一個人在用陳腐哲理,作別著全班同學。那時候關注的是某個女同學肯不肯送我一寸黑白照片,她果然沒送,我威脅要在屬于她的一寸空白處,畫個青面獠牙臉,可還是沒有畫,因為她兇,所以我不敢。
高中我過得虎虎生風,全部七十多人我成績排五十一,可是這不妨礙我在班中發展了一多半的女生成為詩人,依仗語文課代表的優勢。刊物叫《好望角》,詩集叫《風從海邊來》,我的筆名都叫尋海,悶騷得足以成一系列。當然我們念念不忘的都是南中國海,是掛歷上才有的曼妙景象。全民皆詩的好處是畢業時候沒人朝我討要格言了,她們自己就會制造警句——“車輪般旋轉/車燈般迷離的/記憶啊”,還有“離別時,夜的衣衫正灑滿星星。”
現在想想我們對詩歌的迷戀,未必不是對離散的抗爭,就像怡紅公子喜歡和大觀園的姐妹聯句,他以為只要韻腳還多吟詠未斷,一切不測與變故就只能徘徊天邊,不敢近前。
大學畢業又不怎么感傷了,因為我留校,而大多數同學也都留在北京,圈子小,抬頭即見。再過了一個夏天,我才聽到一首叫《再見》的歌,也認識了一個叫金剛的朋友——
“走吧走吧/你在一夜之間就走得干干凈凈,不許我送行還不許我自作多情/關上窗戶關上房門關上星空還要關上彼此的眼睛/這一夜你的慌亂讓我前所未有的鎮定/這一夜地獄歡歌笑語天堂白雪飄零/滿山的杜鵑花哪一朵你會為我摘下/滿城的風和雨哪一句是我該相信的話/你讓我回憶的我讓你忘記的都通通作罷/什么時候你回來,我們再清清白白的成家/什么時候你再為我留一頭長發/親愛的人,再見再見”
一次次回味這首歌,我開始懷疑——我真的畢業了嗎?一次次向往事道別,從回憶中動身的人,他是否還有地方好去呢?
標簽: